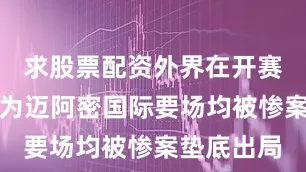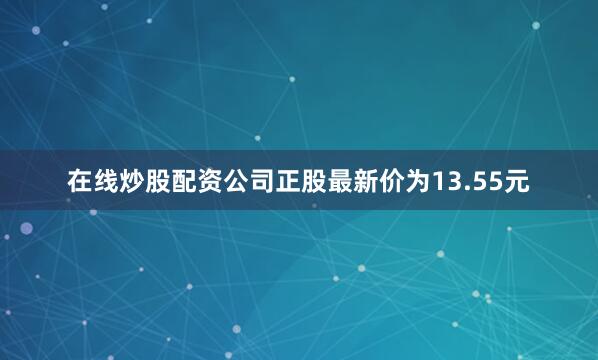白宫方面近日高调宣称,一项与日本达成的贸易协议是美国制造业的“历史性胜利”。他们认为这份协议能创造大量就业,打开市场。但奇怪的是,这份“胜利”宣言并未让美国本土三大汽车制造商——通用、福特和斯特兰蒂斯——感到振奋,反而引来了他们的强烈不满。
特朗普政府对此协议的官方定调是,它用15%的新关税取代了之前放话要征收的25%关税。白宫新闻秘书甚至称之为“历史性突破”。他们的描绘中,这份协议将为美国带来数十万个就业机会,并有效打开日本市场,大幅缩小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。
连日本首相石破茂也公开证实了协议细节,提到汽车部分将面临12.5%新增关税,加上此前2.5%,总计15%。此外,协议还包括日本增加进口美国大米,并承诺向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,同时取消阻碍美国汽车在日本销售的各项法规。这听起来确实像是双赢的局面。

然而,就在政府部门高唱凯歌时,美国汽车产业内部却警报声四起。美国汽车政策委员会(AAPC)主席马特·布朗特毫不客气地指出,这份协议对美国本土汽车产业和工人来说,非但不是胜利,反而可能把他们置于极其不利的竞争地位。
马特·布朗特的担忧,直指关税结构的核心不公。这份美日协议对日本进口汽车只征收15%的关税。但要知道,美国自身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等地的汽车——这些通常包含更高比例美国零部件的车辆——却征收着高达25%的关税。
这种落差令人费解。那些越是“美国制造”、越是深度融合北美供应链的汽车,反而可能因为关税而面临劣势,甚至特朗普还曾扬言要将对墨西哥汽车的关税提高到30%,对加拿大提高到35%。相比之下,日本进口车几乎不含美国零件,却享受着较低的税率。

更别提,美国政府此前已实施普遍的进口汽车关税政策,自某年4月3日生效。而且,对钢铁和铝材还维持着现行的50%高关税。这些额外的负担,都实实在在压在美国本土车企的成本上,加剧了他们的经营困境。
这种结构性的关税劣势,已从理论争议变成了沉重的财务负担。数据显示,自某年4月3日那项25%的普遍关税生效以来,所有美国汽车制造商的成本预计因此增加了1077亿美元。三大汽车巨头就承担了其中419亿美元的巨额成本。
财务报告清晰地揭示了关税带来的实际亏损。通用汽车明确披露,某年第二季度,公司仅因关税一项,就遭受了高达11亿美元的损失。斯特兰蒂斯同样透露,受特朗普关税影响,他们已损失3亿欧元(约合3.52亿美元),并被迫削减出货量、压缩产能。

斯特兰蒂斯公司甚至悲观预计,美国汽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的负面影响将进一步扩大,这种压力可能会持续到2025年下半年。这表明,美国本土汽车制造商所面临的财务困境,并非一时半会就能缓解的短期挑战。
这样的情况并非孤例。此前,AAPC就曾强烈批评特朗普政府与英国达成的贸易协议,那份协议允许英国车企每年可在10%关税下向美国出口10万辆汽车。AAPC认为,这同样损害了美国本土汽车产业的利益,显示出某种反复出现的政策模式。
当然,国际车企对这份协议的态度截然不同。代表丰田、本田、日产等主要日本及其他国际车企的行业协会“Autos Drive America”就对协议“感到鼓舞”。他们认为,协议带来的确定性有助于他们规划更大的投资,进一步扩大在美国的生产基地。

事实上,国际车企过去30年在美投资已超过1240亿美元,并且在过去两年,其在美国的产量甚至超过了美国本土车企。iSeeCars分析师卡尔·布劳尔也直言,新协议为日本汽车制造商提供了短期运营成本优势,这种优势甚至可能优于部分高度依赖海外供应链的美国本土汽车。
尽管白宫声称协议将打开日本市场,但美国汽车政策委员会主席马特·布朗特对此仍持怀疑态度。毕竟,包括美国、欧洲和韩国在内的外国汽车制造商,在日本市场的份额长期以来仅有可怜的6%。仅凭一份协议,能否真正撼动这种根深蒂固的市场格局,仍是未知数。
归根结底,这项被描绘为振兴美国制造业的“胜利协议”,其内在的关税结构却制造了一个显著的悖论。它看似在推动贸易,实则却可能通过对日本进口汽车的“优惠”,间接惩罚了那些与“美国制造”深度融合、美国成分含量更高的产品,加剧了本土汽车巨头的困境。

这无疑凸显出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,贸易政策在追求宏观目标时,可能不经意间忽视微观层面的复杂性与具体产业的结构性差异。政策的初衷与实际效果之间的错位,无疑为未来美国贸易策略的制定,敲响了警钟。
盈昌配资-股票上杠杆资金-股票市场配资-如何配资炒股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